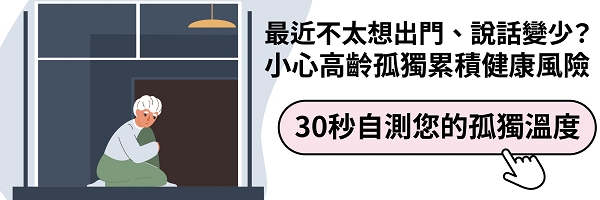2026-01-10 養生.抗老養生
搜尋
Live well
共找到
3
筆 文章
-
![]()
-
![]()
2021-09-27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皙福先生與夫人結縭60年,確因癌末比她先一步離世 悟出「讓我們珍惜活著的每一天!」
Tell me, what is it you plan to do with your one wild and precious life? Mary Oliver【編者按】這星期我們難得的收到了三篇來自不同背景的醫師寫出他們「跨越醫病之間的高牆」的經驗。一位在美國行醫多年的癌症專家寫出與一位老年癌末病人溫馨的互動,悟出「讓我們珍惜活著的每一天」。另一位醫師因為遇到相當有主見、不容易與醫護人員溝通的病人,使他想到「為什麼不考慮誠心接納,順著病人的主張來進行,再加上持續耐心和關懷,設法探索他的內心世界?」。最後一位醫師生病後,自己注意到身體變化,提醒醫療團隊考慮其他可能性,同時也要避免妄作推斷,誤導主治醫師或醫療團隊,才能做一個稱職的病人。皙福先生皙福先生有嚴重的貧血,白血球數也低,去年初夏骨髓檢查發現是「骨髓增生不良」(myelodysplasia)而且骨髓裡的芽細胞(blasts)數量已經瀕臨血癌的程度。皙福先生剛過81歲生日,過去得過攝護腺癌及黑色素瘤,都是開刀痊癒。骨髓增生不良卻是一個很難纏的病。一年多前,我跟皙福先生第一次討論化療建議與治療計畫時,剛好我的同事有個病人跟先生年紀相仿、氣質相近(耳聰目明又手不離卷),也住在同一個鎮;貝克先生患有血癌已經接受化療半年左右。取得雙方的同意後,我介紹他們認識,可以交流經驗。皙福先生每週至少來我們的診所一次做抽血檢驗,化療一個月打五天。一開始,一個月要輸血一兩次,病情也保持穩定了一年左右。皙福先生的夫人因為失智,已經在離他家隔街的一個療養院住了幾年了。他們有三個子女,都住在離他們驅車可至的城鎮。皙福先生非常的獨立,也非常能幹。有一回,因為腹谷溝疝氣卡住,疼痛不堪,在急診室過了一晚,所幸,那段腸子又慢慢縮回腹腔,也迴避了緊急開刀的需求。因為他的血液疾病,開刀的風險很高,外科醫生建議他買一種專門設計給腹谷溝疝氣穿戴的護帶,防止腸子再掉出來。皙福先生從網路訂購護帶,發現不好用,把貨品退還,換了另一個護帶,又不合用,返返複複至少四次才找到一個有效又好用的護帶;之後,疝氣的問題再也沒有發作。這樣的耐心與堅持,讓我非常的欽佩。皙福先生來門診時,總是帶著他的iPad 以及從圖書館借的書。他使用iPad記錄他的病史資料進程,也經常搜尋閱讀相關醫療資訊。他也很會適當的使用他的iPhone 或iPad與他的醫師聯絡。記得一年前,他的小腿上有個傷口,皮膚有點發紅;因為事情發生在週末,在電話上問了他的症狀後,我建議他照個照片,把影像傳給我看,再決定需不需要用抗生素。透過這種方式,在過去一年,我們迴避跑急症室的一般做法,處理了舉凡小傷口,尿道感染及輕微便血的狀況。我的iPhone有好幾張他傳給我的大便上有小量凝固鮮血的照片!我特別欣喜的是皙福先生的好奇心及好學的態度。每次我跟他解釋病情,包括骨髓的正常功能、為什麼他的血球數很低,正常的血球壽命,以及輸注的紅血球能維持多久等等。他總是聽得很專注,也提問很好的問題。我們也常常交換我們正在閱讀的非醫療書籍的心得,以及點到為止的嘲弄川普政府的種種荒誕事蹟。今年的四月初,他向我請了兩個禮拜的假,搭飛機去亞利桑那州去處理(賣掉)他在那裡的一個房子。他跟他的夫人過去每年到那裡過冬,他要去把一些家庭照片及紀念品,裝上他的舊車子開回新罕布夏州;那是將近4300公里的距離!「阿隆(皙福先生的名字),你確定要自己一個人開車嗎?為什麼不坐飛機回來呢?」「沒問題的。我想把我的舊車開回來送給要去上大學的孫子。我跟我太太過去都是開車往還,聽有聲書也容意打發時間,累了就找旅店休息。」我們安排在他出發前輸血,回來後回診驗血,也都平安無事。今年的五月及六月,皙福先生兩度在化療一週後因發高燒住院。特別是六月那一次,他有大腸桿菌的尿道炎及菌血症;剛住院時因為意識不清,生命徵象不穩定而住入加護病房。幸好他對抗生素的反應很好,一兩天後就度過危機,但是體力也耗損了不少。有一天,我去醫院看他,皙福先生完全不知道我前幾天也天天訪視他。當我跟他説明發生了什麼事,他看著我眼淚盈眶地説:「I don’t know what I do without you.」(我不知道沒有你要怎麼辦!)之後,皙福先生的骨髓切片檢查跟以前沒有什麼變化,但是我判斷他的骨髓疾病已經惡化,輸血需求增加、感染症變嚴重,血小板數也下滑。皙福先生在波士頓的 Dana Farber Cancer Institute的腫瘤諮詢醫師跟我討論後,建議換一個新上市的口服藥。一週前,我跟皙福先生説明換藥的理由(病情已經惡化)、治療的目標(穩定血球數,減少輸血需求)。我也很坦誠地告訴他,如果我們很幸運的話,他也許還可以有一年左右的存活期。通常醫生在告訴病人他們有限的生命時,接下來常常用的一句話是“Get your affairs in order.”(把身後的事都交代好)。我説不出口。停了一陣子後。皙福先生凝視著我,平靜地説他昨天已經去找他的律師安排一些事情。我們又討論了這個疾病惡化時常見的併發症,及致死因素;許多病人是因為嚴重感染而過世。面對著這位我很尊敬喜歡的病人講這些很傷感,但不得不説的事,雖然表面上卻必需很平靜、專業,像在給學生上課一樣,心裡其實很難過。我給他一份這個新藥的資訊,並且説明藥價可能會非常昂貴,我們的社工師會幫他找財務協助,大約會花幾個星期的時間才能拿到這個藥(Ivosidenib, an IDH1 inhibitor)。昨天,皙福先生回來他每週定期的驗血。我們發現Ivosidenib的自費價格每個月超過3000美元,社工師還在努力尋找財務支援。這樣天價的治療,任何有點思考能力的人都會問「值得嗎?」。皙福先生自己讀了一些資訊,也思索了許多問題。他的第一個質疑是 Ivosidenib用在血癌的臨床實驗,病人的中存活期(median survival,50%病人的存活)是13個月。我上週告訴他如果我們很幸運的話,他的存活期還可能有一年左右,用不用藥似乎沒有什麼差別。我告訴他,這個藥可能會減少他的輸血需求(65%病人用藥後不再依賴輸血),存活期也有可能遠超過13個月。他也可以選擇支持療法,也就是不用藥物,只接受輸血。當血小板數很低,輸血的需求到了一週兩三次的情況,有的病人可能選擇安寧治療。「記得貝克先生嗎?他在藥物治療失效後,選擇放棄輸血,只做居家安寧。」我説。「是嗎?」雖然他們只見過一次面,皙福先生記得這位儒雅的病友。「因為嚴重貧血,體力會很虛弱,沒有行動能力,甚至會呼吸困難。安寧護士會用嗎啡讓病人保持舒適,慢慢地睡著離去。」我們談了居家安寧需要有家人全天候陪伴,住院安寧可能有病房費的負擔。皙福先生早已想好這個問題。他太太的療養院也有安寧病房,經濟上也沒有問題。之後,我們沉默了一陣子。「 Are you sad or emotional? 」(你很難過嗎?)我問。其實,我是在説我自己,因為我捨不得這位像知己般的病人離開。我們都眼淚盈眶。他沒回答,只是伸出手跟我碰拳(fist bump,因為疫情期間,人們迴避握手或擁抱)。不朽人生前兩天開車時,在公共電台聽到一則感人的故事。一位第一次懷孕的媽媽莎霞,在生產前就知道她的同卵雙胞胎,一個是健康的,另一個患有無腦症。醫生告訴她,無腦症的孩子可能會胎死腹中,或出生不久後就死去。她悲傷的心情可以想見;到底自己做錯了什麼,吃了什麼不該吃的東西,或做了什麼不該做的事,才導致胎兒的異常發展嗎?她的無腦症兒子出生後六天過世。她跟她先生同意將孩子的一些器官組織捐給學術基構做研究。捐贈的同意書説明家屬將來沒有權利尋求研究結果或任何賠償。兩年半後,她的兒子有一天問她,弟弟是不是在天堂裡?他在那裡快樂嗎?這樣的童言讓她有個衝動,想知道她去逝的孩子現在怎麼樣了。剛好過了幾天之後,她到波士頓出差。她知道兒子的眼角膜是捐給哈佛大學的研究機構,就打了電話過去,説明了自己的身分,請求一個造訪研究室的機會。接線生愣了一會兒,因為她從來沒有接到過類似的請求,但是她很熱心的幫忙,莎霞造訪了哈佛;帶她參觀的人也引她見到眼角膜研究室主任。他跟她解釋,新生兒的眼角膜細胞比成人的細胞有再生能力,但是器官的來源很稀罕、珍貴。「妳兒子的眼角膜細胞在我們研究室裡生長著。將來會造福很多人。」那一刻,莎霞覺得她的心幾乎要跳出她的胸口!「我的兒子在人間!」 「他在哈佛,他進了長春藤大學!」之後,莎霞全家人又陸續造訪了其他研究機構,去了解兒子的臍帶血細胞、視網膜及肝臟都用於哪些研究。誰知這個只「活著」六天的生命,變成永恆不朽呢!人生好走當我們告別人間,房子、車子甚至傳家珠寶可以留給子孫後代;但是詩人Mary Oliver問我們 What have we done with our one wild and precious life?皙福先生留給他的家人和我的至寶,將是他的智慧、精神與思想價值。後記當我告知皙福先生我以中文寫了他的故事,他問我能不能給他一個英文版。看了我特別為他寫的英文翻譯後,他寫了很長的電訊給我。他和他的夫人結縭60年,她很依賴他,也很需要他的陪伴(companionship)。皙福先生覺得自己很有福氣,生在很好的家庭;他跟他的夫人旅遍世界;他們有很好的兒女子孫,一生結識了許多好友;真是沒有什麼遺憾了。他卻從沒料到他會先他的夫人一步離世。他並不懼怕死亡,而是捨不得她孤單。我告訴他我完全了解他的心情。我在網路找到林覺民與妻訣別書的中英對照,傳給皙福先生。他傳給我 Sullivan Ballou letter ,一封美國內戰陣亡軍官寫給他即將喪夫的妻子的告別信。那幾天,我的心滿溢著感動,為人間的真情摯愛哽咽無語。適逢美國紀念911恐攻二十週年,許多電視節目回顧那轉眼間灰飛煙滅的無數生命,令人感念生死的無常。不管年輕健壯或老病潺弱,我們在塵世的日子總是有限的,因此,讓我們珍惜活著的每一天,live our one wild and precious life as well as it can be.
-
![]()
2021-04-02 新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醫院裡不可或缺的存在! 美國麻醉科醫師照顧新冠肺炎病人的內心世界
【編者按】本週的主題是「麻醉科醫師的內心世界」。麻醉科醫師的工作不只對社會大眾,對其他醫療團隊成員也都相當神秘。第一篇文章來自年輕的麻醉科醫師介紹這項專業;第二篇來自曾經擔任「麻醉風暴」醫療總顧問的麻醉科醫師以台灣經歷SARS的背景寫出這篇文章;第三篇來自一位美國麻醉科醫師友人與編者分享她在美國照顧新冠肺炎病人的衝擊下,寫出對麻醉科醫師生涯的諸多感觸。事實上本週的主題就是因為這位美國友人的文章引起我們之間的討論,非常高興她欣然同意我們轉載這篇發表於史丹佛大學醫院刊物的文章,並附上一位外科醫師的中譯。這也是「醫病平台」首次轉載英文原作與中譯的嘗試。我是個不可或缺的工作者。我從未理解自己有多麼不可或缺,也未曾如此描述自己,直到冠狀病毒大流行。數百萬計的人們因為居家隔離的規定而無法出門工作,然而我必須如此:我是個麻醉科醫師。當我穿越檢疫站,與其他不可或缺的工作者走入醫院時,我想起了我的單親媽媽在我與姐姐小時候所灌輸給我們的觀念。當我們在一片漆黑中,無法付出電費時,她說:「不想過這種日子的話,就好好接受教育。」我們從未無家可歸或飢腸轆轆,然而我們的公寓狀況並不好——牆壁滿是坑洞、在樓下的女子被強暴後加裝在後窗外的鐵桿。我的母親並未向房東抱怨,她教我們:「絕不要開口求援,世界不是為了救你而存在的。」若我沒有足夠的錢買公車票,我也不曾開口祈求他人施捨。從小,我便靠著裝信和當保姆賺錢。另一方面,我亦有著難以置信的多采多姿豐富童年。我的母親是一位服裝設計師,因此我曾在排演時從劇院的舞台側面觀賞過《厭世者》(莫里哀)。我也鍾情圖書館。雖然我害怕圖書館員,但那是一個放學後能夠安全待著的地方。安全,是除了賺得溫飽之外另一個我反覆學習的人生課題。在家裡,我與姊姊會將從圖書館借來的書在地上排成一列,假裝一越過便會落入深淵。但我們知道—或至少相信—那深淵並不存在當我的母親說「受教育吧」,我聽從了。我進入了一所傑出的公立高中,整個費城最優秀的孩子都來就讀的重點學校。大學時,我獲得了全額獎學金攻讀生化。我原本預計進攻博士學位,然而,在某個暑假工讀時,我認識了一位博士後研究員,他已到達我認知裡的教育巔峰。他告訴我,明年他將失業。這讓我大吃一驚。從那刻起,我知道我必須尋找新方向,找個能永遠不愁沒工作的領域。同一年稍晚,當我行經宿舍外某個據說要成為《愛情故事》的電影拍攝場景時,我忽然頓悟了。每個人都會生病,即使是愛情故事的女主角艾里‧麥克洛也一樣。若我成為醫生,我總會有工作的。發現新大陸啦!當然,在面試醫學院時,我無法明說我的動機。就算我再熱愛科學,我知道促使我選擇這條路的原因是我知道我永遠有工作。時間快轉過數十年醫學院與麻醉生涯。雖然承擔著壓力造成的心理健康風險以及無數種有點小傷殘就能讓麻醉科醫師一無是處,但我每天都有著安全又保固的工作(媽,你一定很驕傲!)如今,這份工作的安全性也變了。穿上加強防護的個人裝備,我檢視這些在我將進行的呼吸道處置時(這使得病毒更加容易傳播)保護我的堡壘。我短淺而費力的在N95口罩和面罩裡用嘴呼吸,在不透氣層與雙層手套的重重阻礙下緩慢的移動我的四肢,彷彿月球漫步。我大聲地請護理師離開房間,而有時我必須扯開嗓門才能讓呼吸治療師聽到。我俯視著驚恐—或極度驚恐—的病人。我是他們最後一個見到的人,在我給予麻藥並在在他們聲帶之間放入一根塑膠管子之前。「我要給你一種會很想睡覺的藥」我說,「也會從氣管內管給你幫助你呼吸的藥。」「我們會好好照顧你的。」這些話,在情非得已的大吼下顯得格外苛刻。回首過往,我才了解,在愛滋、SARS、MERS和伊波拉病毒的疫情下,我曾經是個不可或缺的工作者。但因為我所居住的地方、不多的暴露狀況,以及這些病毒的傳播方式,我並不像現在一樣總是恐懼相伴。自古以來就有著飛機機長與麻醉科醫生的類比;我們將起飛和著陸和麻醉的各個階段相比。這樣的比喻是有好處的——這也是為何原本為機師訓練而設計的模擬與溝通訓練,現在已成為麻醉教育的標準程序。不過,兩者之間有個相當大的差異:假如墜機,機師也難逃一劫;而麻醉要是出了錯,只有病人會死去。當大聲的急診呼叫從天而降時,作為新冠肺炎呼吸道小組成員的我,在抵達急診前抓起我們裝在專屬行李箱裡的工具、回覆小組成員的簡訊、並戴好我的N95口罩和護目鏡—剩下的器具必須在病人候診區外先包覆並檢查好—我深切的感受到(幾乎是全身上下的每個細胞都感受到),如今一切都變了。在新冠肺炎的肆虐下,我有可能會死。若我把病毒帶回家,可能會害死我摯愛的人。這,就像是一場緩慢,卻無可避免的飛機失事。疫情中的某天,一位比我年輕的同事(事實上現在所有人都比我年輕)來找我。他告訴我自己的心跳快到每分鐘130下,但除此之外沒有不舒服。他的體溫、心律、血氧、和血壓都沒事。我告訴他:「沒事的,回家、喝點水然後好好休息。我會照顧你的病人。」他回家後心跳便恢復正常了。這是焦慮,不是病毒。這種焦慮程度在新冠肺炎爆發之前從未發生在他身上。不只是病毒威脅著我們,恐懼也是。直到現在,我還未認真思考過成為不可或缺的工作者的危險。但是我的母親讓我擁有應付大量壓力的餘裕。她教會我我是被愛的。也許,看著她獨自撐過這一切,她教會我不要重蹈她的覆轍。她教會我活到老學到老,而我從同事身上學到向他人尋求幫助這一點,是我人生中最無價的一課。示弱無妨,告訴賣公車票的老師自己沒有足夠的錢也無妨。我從這次疫情學到的是:我們榮辱與共。我們都是被需要的。在這世界上我們並不孤單。此外,開口求援—尤其你是個不可或缺工作者時—絕對是件不可或缺的事。ESSENTIAL (By Audrey Shafer)I am an essential worker. I just didn’t realize how essential I was, and never would have described myself that way, until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Millions cannot go to work due to shelter-at-home rules, but I have to: I’m an anesthesiologist. As I pass through the checkpoint to enter the hospital with other essential workers, I am reminded of what my single-parent mother instilled in my sister and me when we were little. While we sat in the dark, unable to pay the electricity bill, she said: “If you don’t want to live like this, get an education.”We were never homeless or hungry, but the apartment was also not well maintained, with holes in the plaster, and bars on the back windows after the woman who lived on the floor below us was raped. My mother never complained to the landlord – she taught us “Never ask for help, the world is not here to help you.” If I didn’t have enough money for a packet of bus tokens, I was not to ask anyone for a handout. At a young age, I stuffed envelopes and babysat to earn money.On the other hand, I had an unbelievably rich childhood – my mother was a costume designer and I sawThe Misanthrope and Endgame from the wings of the theater during dress rehearsals. I also loved the library. Even though I was afraid of librarians, the library was a safe place to go after school, and safety, besides a livable wage, was another lesson drilled into me. At home, my sister and I played a game with our library books, placing them along the floor and pretending that if you stepped off them, you sank into a watery abyss. But we knew, or at least we believed, the abyss wasn’t real.When my mom said get an education, I listened. I went to an outstanding public high school – a magnet school that drew the brightest kids from all over Philadelphia. I attended college on full financial aid and majored in biochemistry. I planned to get a Ph.D. but during a summer work-study job, I met a post-doc – someone who already had achieved what I was convinced was the pinnacle of education. He told me he didn’t have a job the next year. This blew my mind. In that moment, I knew I needed to seek a new direction, something where I could always have a job.Later that year, I had an epiphany while walking outside my dorm at a site rumored to be a film location for Love (‘means never having to say you’re sorry’) Story. Everyone gets sick, even Ali MacGraw’s character. If I became a physician, I’d always have a job. Eureka! Of course, in medical school interviews, I couldn’t come clean about my reasons. As much as I loved science, I knew I had chosen this path because I felt I would always be employed.Yet, at medical school, something changed. Love happened in an unlikely setting. I felt strangely fatigued during my anesthesiology elective, but enjoyed the people and culture of this hidden part of medicine. Delirious and febrile from mononucleosis-induced hepatitis, which I did not initially know I had, I fell deeply in love with the quirky, fulfilling specialty of anesthesiology.Fast forward through decades of academic anesthesiology practice – and, despite risks to mental health from stress and the myriad ways in which a minor disability could render the anesthesiologist useless, I had (you’d be proud, mom!) a safe and secure job every day of my life. But the job and its safety have changed.Donning enhanced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I check the barriers protecting me as an anesthesiologist during and after the airway procedures I will perform - procedures which make the virus even more contagious. I mouth breathe, pant really, in my N95 mask and hood, and, encumbered by impermeable layers and double gloves, move my limbs slowly as if I was in a phony moon landing scenario. I loudly ask the nurse to leave the room; sometimes I have to shout to be heard by the respiratory therapist. I look down at my frightened or too-far-gone-to-be-frightened patient. I’m the last person they will see before I push sedatives and place a plastic tube between their vocal cords. “I’m giving you medicine to make you very sleepy,” I say. “Medicine to put in a breathing tube to help you breathe. We will take good care of you.” It sounds harsh because I have to speak so loudly.I understand, retrospectively, I was an essential worker through HIV/AIDS, SARS, MERS and Ebola. But because of where I live, my limited exposure, and how these diseases are transmitted, I never felt the fear that is my steady companion now.There is a longstanding analogy involving airline pilots and anesthesiologists, which compares take-off, flight, and landing to stages of an anesthetic. There are benefits to the analogy – it’s why simul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raining, developed for pilots, is now standard in anesthesiology education. There is a big difference, though: if the plane goes down, the pilot dies too; but if the anesthetic goes awry, only the patient dies.As another overhead code call to the emergency room blares, and I, on the COVID airway team, grab equipment we pack in wheeled suitcases, respond to texts from team members, and don my N95 and eye protection before hitting the ER – the rest of the equipment will need to be donned and checked outside the patient bay – I realize, almost cellularly, that things are different now. With COVID-19, I could die. Or I could cause my loved ones to die if I bring the virus home. It would be like a slow but inevitable plane crash. A younger colleague (and now they are all younger) came up to me one pandemic day. He said his heart rate was 130 but he otherwise felt fine. His temperature, heart rhythm, oxygen saturation, and blood pressure were fine. I told him, “It’s okay, go home, drink some water and relax. I’ll do your case.” He went home and his heart rate normalized. It was anxiety, not virus. This level of anxiety would have never happened to him pre-COVID. It’s not just the virus that threatens all of us, it’s also the fear.Until now, I hadn’t truly thought about the danger of being an essential worker. But my mom equipped me to deal with enormous stress. Taught me I was loved. And maybe, in watching her go it alone for so many years, taught me to live a life different than hers. She taught me to be a lifelong learner, and what I learned from my colleague, to seek help from others, is one of the most valuable lessons of my life. It’s okay to be vulnerable, it’s okay to tell the teacher selling bus tokens you don’t have enough money.What I learned in the pandemic is this: we are all in this together. We are all needed. None of us is alone in this world. And asking for help, especially if you are an essential worker, is, ultimately, the essential thing to do.Audrey Shafer, MD, is a Stanford Professor of Anesthesiology, Perioperative and Pain medicine, the Director of the Medicine and the Muse program and the Co-Director of the Biomedical Ethics and Medical Humanities Scholarly Concentration. She is an anesthesiologist at the Veterans Affairs Palo Alto Health Care System. (原文出自https://med.stanford.edu/anesthesia/community/arts-and-anesthesia-soiree/covid-19-highlight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