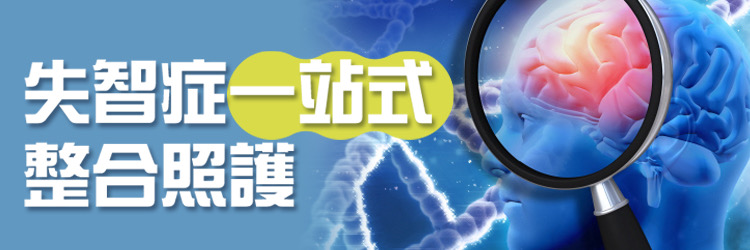2023-06-09 焦點.杏林.診間
醫病平台/同理的載體
編者按:本週的主題是「醫學與文學」。第一篇文章來自曾在醫病平台發表過中譯散文的史丹佛大學醫學院麻醉科教授Audrey Shafer。她最近在一場大病之後,以「醫學是這樣」為題,寫出學者、師者、病人、醫者交錯不息的照護角色,並由上次同一位本身也是醫師的譯者,翻譯成同樣令人感動的中文詩。→想看本文我們也邀請兩位具有深厚人文修養的醫師分別寫出他們對醫學與人文的看法。一位是長年旅居美國的名作家兼退休精神科教授,寫出他對醫師成為良醫的一體兩面「治病」 與「醫人」的重要,而語重心長地發表他對當代醫學教育,越來越注重治病的層面,而幾乎完全忽略了「人」的隱憂。→想看本文一位對「醫學人文」與「科學研究」都有深厚造詣的年輕醫師介紹幾本他所鍾愛的探討疾病、死亡、歷史的好書,而深深體會身為醫師,我們不僅要了解疾病生物上的機制,更要了解罹病的人與他周遭的社群是如何互動,而文學作品正是提供這類分析或敘事最好的媒介。作為醫者,我們總被教導著要去同理病人,要「視病猶親」、「感同身受」,將眼前正在受苦的陌生人視為自己的親人,用自己的身心去感受他們的疼痛,但我們真的做得到嗎?要如何將一個見面五分鐘的病人當作至親,又如何在從來沒有親身體驗此病症的情況下去感受對方的不適?西方人在試圖表示同理時有一句饒富況味的話,「我只能想像你的感受(I can only imagine how you are feeling)」,我永遠無法親身體會,我只能想像,而這樣的想像正是同理的基礎。歷史學家哈拉瑞在其鉅作《人類大歷史》曾提到,人類從群居動物邁入文明社會的一大關鍵正是神話的產生,因為共同相信著某些想像故事,人類得以建立比起仰賴血脈相連的部落更為龐大的文明,建立起國家、民族的共同體。而承載著這些想像的是故事、是文學。透過了解他人的生命故事,透過對於痛苦虛構、非虛構的描寫,透過對於疾病的白描隱喻,我們漸漸才能夠切身的感受到一位陌生人的痛苦,讓同理成為可能。在行醫之路上陪伴著不少癌症病人走完生命的最後,當在病榻旁說出死亡宣告時,家屬的潸然淚下總是使我不知所措,彷彿是那個空間中的他者。的確,我不理解癌症如何吞噬生命,也不理解至親因病離開的苦痛——直到我讀到《當呼吸化為空氣》這本書。《當呼吸化為空氣》是一位被譽為天才的神經外科醫師的自述,這位作者正是我嚮往著成為的模樣,左手執筆右手執手術刀,又會看病又會作研究,這樣一個近乎完美的人在住院醫師訓練完成之際確診了末期肺癌。他以極為細膩靈巧的筆觸帶領著我走進他的世界,那些對於醫院的描寫處處引人共鳴,而在逐漸認識熟悉作者之際,他開始敘寫末期癌症對於他與家人的影響。他曾經的內科醫師同事變成了照顧他的醫師,他不再有力氣長時間寫作,連敲打鍵盤都會引起劇烈的疼痛,我一頁一頁地翻著,自己的身體彷彿與他一同感受著生命的流逝,直到最後幾章嘎然而止——他在完成此書前就因病過世。而「後記」是他的妻子所寫,寫著他們與家人是如何陪伴著作者在病床上安然地睡去,寫著作者的離世所帶來的巨大空洞,那些場景在腦海裡形成一幕幕無比真實的具象,直至闔上書本的那一刻我才驚覺自己早已淚流滿面。往後的日子裡,在病床旁我總是會不斷想到這本書的場景,那些文字彷彿成為一種載體,承載著我的思緒慢慢地靠近病人。對我來說,文學讓同理成為可能,透過對於疾病的書寫,透過這些描繪,我們能夠把自己的生命經驗與他人的交織,形成新的觀點。文學對於醫學的功用不僅限於共感的形成,更可以是解剖疾病與社會複雜關係的利刃。如同蘇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隱喻》中爬梳著人類基於對疾病的恐懼與迷思所衍生出的隱喻,例如癌症明明是基因與細胞機能上的變異,卻在想像的渲染中變成某種「殺手」或「懲罰」,而不幸罹病的患者彷彿道德上犯了罪,受到「天譴」。這幾年造成全球恐慌的COVID-19同樣也承載著許多文化上的隱喻,彷彿染病的人就是不衛生、不負責任地傳染給他人,而為了控制這樣的疾病我們要「封城」,如同抵禦外侮一般抵禦著構造甚至比單細胞生物還簡單的病毒分子。身為醫師,我們不僅要了解疾病生物上的機制,更要了解罹病的人與他周遭的社群是如何互動,而文學作品正是提供這類分析或敘事最好的媒介。有著再多的反思與體認,我們終究無法完整地感受病人的痛,但或許真正的同理並不是到達某個終點,而是這個不斷嘗試靠近的過程。責任編輯:吳依凡